阅读:0
听报道
作者丨贾想
时隔八年,余华推出长篇新作《文城》,也引发了破圈的赞美和批评。有人说“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也有人觉得《文城》不过纯文学爽文而已。青年批评家贾想认为,归来的余华,骑术依旧高超,但已不是一个骑兵。
“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听到《文城》的这句宣传语,余华小说的忠诚读者、与余华暗自较量的同行、余华的亲友团和余华的敌人,没有谁会不被吊起胃口。在很多人心里,《活着》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最高级形容词,一个文学俘获我们心灵的铁证,一个难以逾越的传播奇迹。因此,这句话让我们对《文城》至少产生了三重期待:像《活着》一样高超,像《活着》一样动人,像《活着》一样好读。
“那个写《活着》的余华又回来了。”听到《文城》的这句宣传语,余华小说的忠诚读者、与余华暗自较量的同行、余华的亲友团和余华的敌人,没有谁会不被吊起胃口。在很多人心里,《活着》已经成为了当代文学的一个最高级形容词,一个文学俘获我们心灵的铁证,一个难以逾越的传播奇迹。因此,这句话让我们对《文城》至少产生了三重期待:像《活着》一样高超,像《活着》一样动人,像《活着》一样好读。
因为这三重期待,整个文学圈子都躁动起来了。又因为某些期待的落空,大家又纷纷争吵起来了。比如,《文城》是名副其实还是乏善可陈?是胜在故事还是输在小说?乃至余华的重复性以及人物、情节、细节的种种漏洞或者光芒,从学者到素人、从艺术风格到技术分析,讨论之充分、耐心、赤诚得罕见。
所以,尽管《文城》已经不剩什么惹人的话题可讲,但这热烈而赤诚的话语场,这有机的喧哗与骚动,还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加入,把只剩骨架的《文城》再啃一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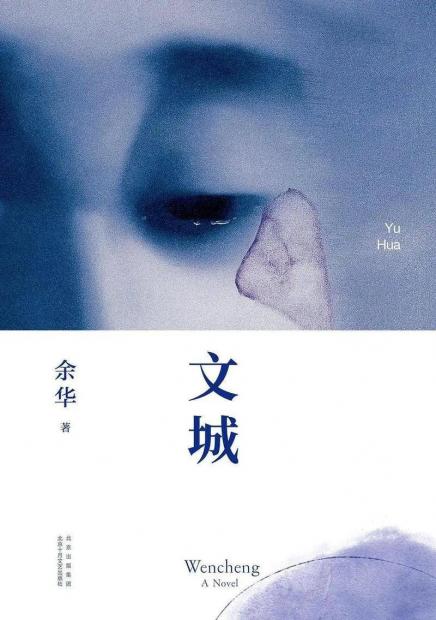
《文城》,余华,新经典文化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3月版
01
简单的语词,匮乏的语言
那么,就从一些小骨头——比如余华的语言,讲起吧。
即使盖住一切信息,只看一小段语言,我们也十有八九猜得中:《文城》的作者叫余华。因为其小说风格,首先就来自那极具辨识度的、直男式的语言。
早期中短篇时代,余华的语言机械、冷漠、不暧昧、不婉转,更不楚楚动人。他热爱动词,热爱动词主导的、推进式的陈述句,排斥形容词,更排斥感性的抒情。他习惯在句子与句子之间安装一个零度的连接词,习惯故意使用一些与肉体不相关的、抽象而干燥的动词:出现了、来到了、开始了、完成了。除了这种冰冷而机械的性感,在《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那里,余华又将诙谐和朴拙揉进了他的语言。
到了《文城》,他的语言不再像往常一样高度统一。机械的性感、沉着的抒情、诙谐的喋喋不休混合在一起,时而凌乱,时而整饬。但无论如何混杂,相比于普鲁斯特那样绚烂的作家,他的语言仍旧是简单的,正如斯坦纳用来形容海明威的那种语言——“简单语词”。

《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
用中学生语词写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曾是余华得意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掌握了以少胜多的辩证法。确实是这样,“少就是多”,胜过“多就是少”。但在《文城》这里,故事整体上并没有做到“少就是多”。相反,很多时候,“少就是少”。比如写林祥福的心理状态——“他心地善良生机勃勃随遇而安。”这整齐的、概括性的四字词语,其实无法穿过神经系统抵达我们的感觉皮层,更休谈激发我们的新鲜感受,也再度让人意识到,余华的语言是封闭的,不是开放的、呼朋唤友的。很多时候,他在营造语词“外观上的生机”,但这种生机和读者无形中催生的“感觉上的生机”,根本是两回事。或许,斯坦纳对海明威的担忧不无道理:“简单语词能够用来表达复杂思想和感情,简单语词也可能用来表达本身就很低级的意识状态。”
另外,在表达他并不熟悉的东西时,余华的词汇明显匮乏,比如小说里的女人小美。男作家可以写好女性吗?至少直男很难(但无法避开)。余华以及绝大多数当代男作家掌握的女性词汇,皆来自他们自身的“凝视”,没有涨破男人的审美系统和认知系统。这涉及到语言上的深度缺陷,涉及到语言革命、意识革命的问题。只是对于男人,余华同样经常重复着过去的词语,像“田野”——“林祥福以田野般的宽厚接纳了小美。”曾经,这样的词也形容过《活着》当中的福贵。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想:余华在学习史诗的语法。他想模仿荷马那种确凿无疑的形容——“欣慰的神色从她眼中流出”,洞察一切的概括——“多年的操劳之累和守寡之苦使她头发发白”,以及煞有介事(仿佛眼见)的真实。他学习史诗,将男人与田野、土地、植物、光放在一起,以获得某种原始意象的加持。
然而,在这个充满疑问的、“目击众神死亡”的现代田野上,史诗的语法还有魔力吗?曾经的史诗之所以引用自然意象,是因为彼时的一切意象都是神造物,于是那些意象也才灵力充沛。如今已是人的时代,那些被神抚摸过的意象正在失去古老而神秘的活力。何况,模仿史诗的语法,还需要经年的功力。
对此,余华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02
不减速的流畅,没防备的眼泪
的确,《文城》像《活着》一样好读。在这个狭窄的意义上,余华是回来了:他的故事一如既往的流畅。我不否认他在叙事上难以掩藏的才华,但这还不够。首先,过度流畅是小说的敌人,因为作者需要过度地取悦;更重要的是,余华的流畅是怎样的流畅,跟通俗文学乃至动作片的流畅是一回事儿吗?
从叙事技巧上看,是有关的。余华的故事和通俗文学一样,其可读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情节悬念(小美突然失踪)和情感悬念(小美爱不爱林祥福)。但通俗文学的流畅,是一种“加法”的结果——不断增设悬念,不断添加欲望和暴力、升级和逆袭的桥段,反复激发读者的爽感,最终变成无法结尾的“爽文”。余华的流畅,则是“减法”的结果。
减掉了什么?至少三样东西:形容、对话、心理描写。
什么是形容?王安忆《长恨歌》的开头四章,尽是形容。比如写弄堂的“暗”:“那暗看上去几乎是波涛汹涌,几乎要将那几点几线的光推着走似的。它是有体积的,而点和线却是浮在面上的,是为划分这个体积而存在的。那暗是像深渊一样,扔一座山下去,也悄无声息地沉了底。”形容是漫长的长镜头,是时间缓慢的散步;形容无法让叙事奔跑起来,相反,在对一间弄堂、一句流言的形容中,叙事被耽搁了。形容是“停下来”。
余华也不写对话。《文城》中好像有对话,但细细看来,多的是马尔克斯那样的单句——判断、命令、祈祷、乞求、忏悔。比如《百年孤独》的这一段:“孩子们至死都记得,由于长期熬夜和冥思苦想而变得精疲力竭的父亲,如何洋洋得意地向他们宣布自己的发现:‘地球是圆的,象橙子。’”这其实是独白,不是对白。在《文城》中,土匪横行的篇章似乎写了对话,但总是在服务情节的前进,是平行的,而非缠绕、旋转、向深处钻孔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里,卡拉马佐夫兄弟之间的辩论才是缠绕、旋转、向深处钻孔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才有力量、平等、触及灵魂。但这样的对话风险太大了,会让故事突然降速,让情感剧烈波动,让设计好的结构奔溃。除非作家把这种风险当做美学上的冒险,否则,屏蔽对话是机智的。
最后,再说心理。古典的托尔斯泰式心理描写,充满了几页几页的自我剖析。这种对自我意识的沉溺,必定会让情节暂停。尽管心理描写对塑造人物性格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在叙事上却是最减速的、最粘滞的,把握起来无比困难,所以基本被追求效率的现代小说家们抛弃了。余华也曾谈到,《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杀害房东的情节启发了他,心理原来全部可以通过动作展示。害怕时眼神会躲闪,兴奋时候会手舞足蹈。的确如此,写动作有时候就是写心理。

2019年,余华参演了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余华热爱叙事的运动,迷恋男性主义的“向前进”,所以他不能允许叙事的减速和停滞。只有经过层层减法,他才能获得他的流畅,获得那种迅疾的风格。这是一种追求效率的现代美学,这种美学让他成为了一个“不减速”的小说家。不减速,所以读得快。但读得快,往往就来不及沉思;来不及沉思,也就来不及防备;来不及防备,就容易流下眼泪。读《活着》时如此,读《许三观卖血记》时如此,到了《文城》这一站,余华依然不肯减速,他要维持我们流泪的惯性。
03
面对死亡的放松和自然
“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小说收尾的部分,余华跳出来,以林祥福的嘴巴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题眼。在这句话中,“文城”从特殊抽象为一般,从地理空间转变为寓言空间,从存在突入虚无。没想到,隐喻的力量,在《文城》的最后突然被余华召唤、动用了。
隐喻的力量,是一种造成深度的力量。它的出现,是为了加深过于实在、具体、单一的艺术。这也是余华的本意吧——加深这个一百年前的民间传奇,让这则凄美的寻人启事不止于凄美。这里面花的心思,品得出。
只是,在小说这种依赖长度的文体中,隐喻这种追求深度的技巧,究竟有多少力量?可以通过一个深奥的隐喻,将本来非常写实的故事变得意味无穷吗?我想,余华在虚实之间一定有过徘徊。一个擅长抽象的作家,不会甘心自己的故事仅仅停留在写实的层面,通过这种方式,他在《文城》中留下了独属于余华的水印。
最鲜明的水印,来自《文城》的结尾。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两个苦命人,一个以棺材的形态,一个以坟的形态,死生契阔,再度重逢。无论如何,这是个漂亮的收尾。读到这里,我们会剧烈颠簸一下。我们不会预料到还有这一招。

电影《活着》剧照
不过因为早就被“剧透”,看到“会面”这个彩蛋,我并没有感受到情感上的那种颠簸。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微妙的变化:这一段对于死亡的交代,突然从余华擅长的浓烈抒情中解脱了(比如对福贵家人之死的书写),显得格外放松和自然。过去的余华面对死亡,要么炫示,要么慈悲,总之态度明确:他要在死亡的书写上展示自己的风格和能力,他要用死亡这一张底牌亮出小说的意义。但这一次,余华似乎不太一样了。他没有在死亡这里多做停留,而是转身上路,让两位亡灵继续离别,让无根的命运继续飘散。
这才是《文城》传递给我的最为重要的讯息。死亡与它的衍生品——苦难、长情、伤害后的慈悲、幸存后的乐观,余华已经太过熟练。今后,他是不是要解放那操弄死亡的股掌,去触碰更加陌生、更具挑战性的艺术材料和艺术题目?
04
余华收起了长枪,离开时代现场
期待落空了也好,没落空也好,读完《文城》,我们没有沉默,没有“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相反,从圈内到圈外,余华和《文城》激活了大家休克的舌头。我们的表达冲动复活了,我们吹嘘、吐槽、赞美、批评、较真甚至角斗,我们乐在其中。《文城》似乎正在成为一个事件,正在从文学领域向公共领域“破圈”,引发更多圈层的读者加入对于作家、文学、艺术、都市、历史、真与假、生与死的讨论。作品本身的好坏,反倒慢慢成为次要的事。
这一次,《文城》没有成为少数精英的瓮中之物,没有卷入文学内部的圈地运动,没有成为“文学内卷”的消耗品,而是属于所有文学读者、属于公共听觉的一个部分。
但回到文本,我们会发现,《文城》其实并没有涉及什么当下的公共议题,相反,其中的议题多数陈旧。这是一个清末民初的故事,与我们隔着一百余年的千山万水。在这个意义上,余华没有回来,相反,他离开了我们的时代现场。他避开了当下的人心、当代的问题。他从小说退回了故事,从生活退回了命运,从当代退回了过往,从叙述退回了隐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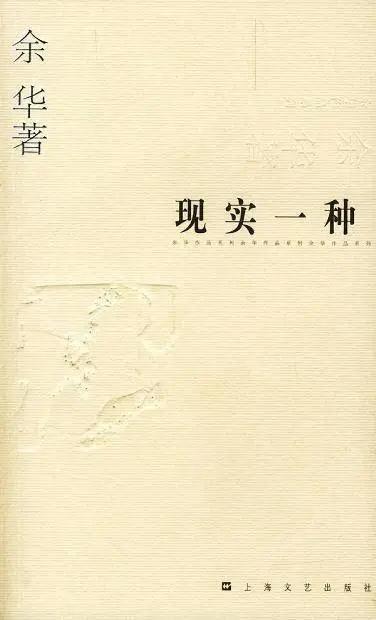
余华的中篇小说集《现实一种》,其中收录了《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
要记得,那个写《一九八六年》和《现实一种》的余华是凶猛的,那个写《兄弟》和《第七天》的余华是勇猛的。那时他把小说当做一把虚构的长枪,直指当代田野上那些疯狂、混乱和荒谬的风车,哪怕艺术上可能会遭受失败。现在,在《文城》里,我们看到余华收起了他的长枪,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掉头转向历史深处那个隐秘的南方,优雅地策马离去。
他的骑术依旧高超,但他已不是一个骑兵。
作者系青年批评家,作品散见于《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福建文学》《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星星》《青年文学》等。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